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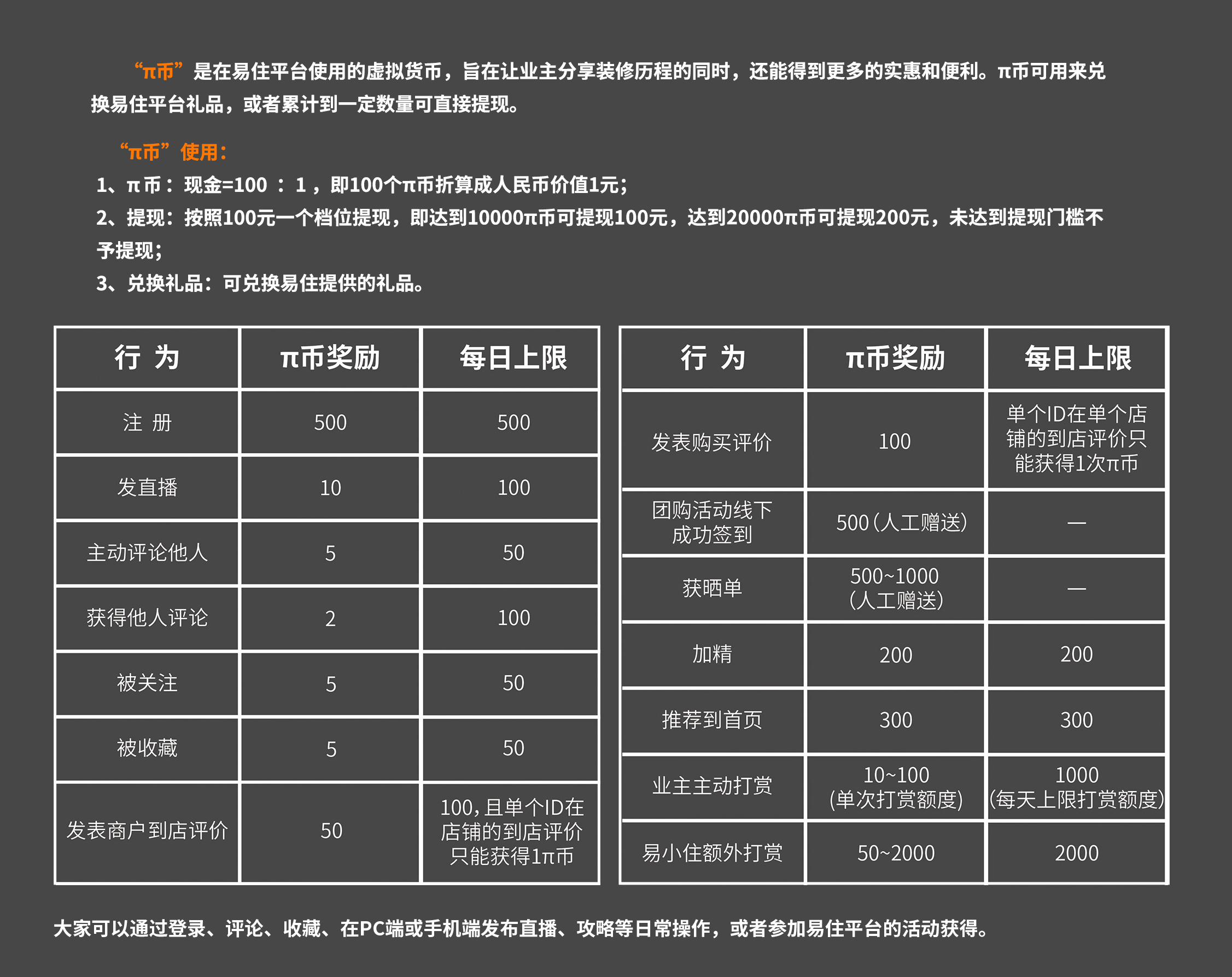
色彩与照明是本次设计的重点之一。我们将运用丰富的色彩对比,突出展品的特色,同时营造出活力、现代的氛围。照明上,除了基础照明外,我们将设置局部聚光、背景照明等多种方式,以增强展品的视觉效果,引导观众的视线。
“半自宅”性质的办公空间,除了以自由平面进行回应,摒弃效率优先、功能明确的布局外,相继伴随而来的是对日常性的引入。相比于标准严苛的工业化生产,日常生活要明显松弛、琐碎、灵活,并允许一定程度的偏离。如果说,工业化生产是一个行业标准体系的代表,那么对日常生活的表达则是连接自我感知与个体精神的神经元通路。在一楼的开放式办公区域,一体成型的水磨石吧台厚重流畅,有如于空间之中生长出来的雕塑体,经由三个连续平缓的弯折形成半围合的状态,增加了空间的延伸性。但一反常态的是,吧台连同其内侧的厨房操作台,以相当的体量占据着一层空间的核心位置,致使办公区域不得不向两侧腾挪。如此一来,作为一种强调,日常生活的公共性被有意识的放大了,整个办公空间的严肃性得到最大消解,还原为一种细腻随性的姿态。
楼梯是另一种形式的表达,它不同于吧台直接指向日常性,而是通过陌生化的方式凸显对日常性的处理。如,以水磨石砌筑起始台步,制造与吧台的互动关联,随后改用悬浮的木质梯步,如枕木一般完成向上的层叠。水磨石的肌理与原木的质感,通过这种接续的处理,产生微妙的通感,日常的知觉经验被唤醒。而楼梯顶端盘坐的佛像,古慈憨然,一种更遥远亘古的经验被触及,表现为非日常的精神性时刻:举头三尺有神明。但随着梯步上升,神明变得可触可即,日常空间又再一次回归。
顶部的天窗不仅有接纳光线的功能意义,更在精神上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符号性指引。天窗具有一定的纵深感,呈现出方形的井状结构,光线的神圣性因天窗克制的尺度而浓缩凝炼,并与楼梯口的佛像形成回应,它们一虚一实,一个指向过去深邃悠远的传统意象,一个抵达更抽象的后现代语境,完成空间从功能到精神的双向表达。
空间关照着身体,情绪松弛而有张力。这一切,也得益于细部以视知觉的方式加以把握。如,与开放式办公区域形成分隔的方形墙体边框,其白色抹灰墙面的抹圆角,不仅凸显墙体的厚度,建立空间层次,同时也增加了墙面的连续性与光影细节。而地面是手工青砖的再利用,以人字纹铺就,细微的浓淡变化与肌理组织,构建着时间的密度,赋予空间回望过去的可能。
沙发座椅被安置于壁炉之前,天窗之下。无花果树依凭着光而生长,人依凭着无花果树而安坐,其后是满墙的书与读物。这是一个无法用单一的功能去定义的空间,它是多元复合的空间,兼顾阅读、会客、办公、休憩、聚会等多重功能;也是建筑学概念里所指的多义性空间,在开敞时开敞,在聚合时聚合,它的独立性与连续性随场景的转换而转换。白天友客来访,交谈工作,处理事务;夜晚来临时,可以独坐安享,与迷离的灯光和音乐为伴。尤其到了冬夜,当壁炉里的柴火烧出哔哔啵啵的声响,一次阅读,一场倾谈,便足够抵挡住一切时光流逝。
